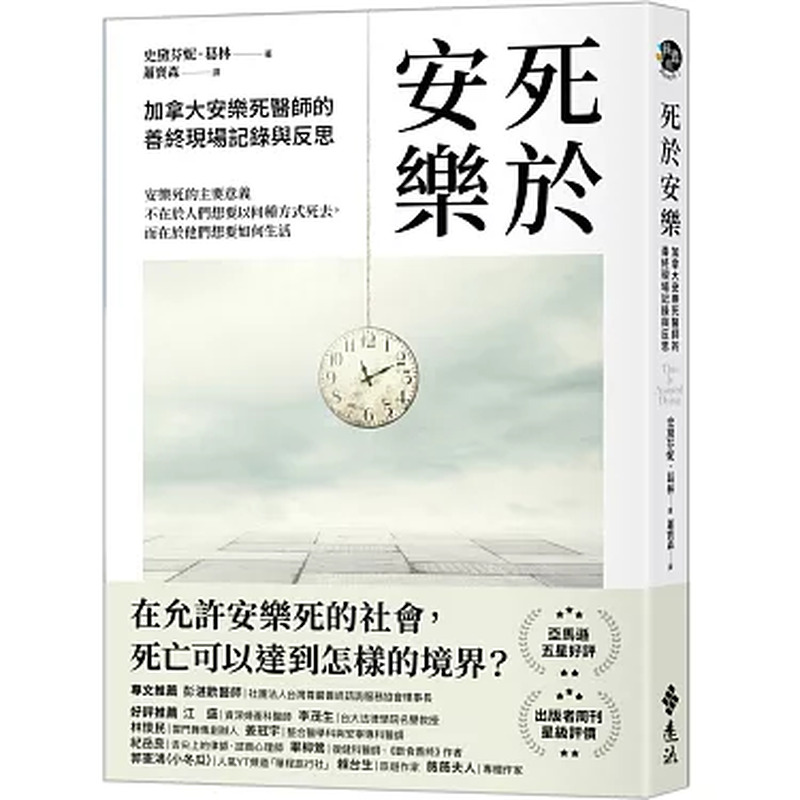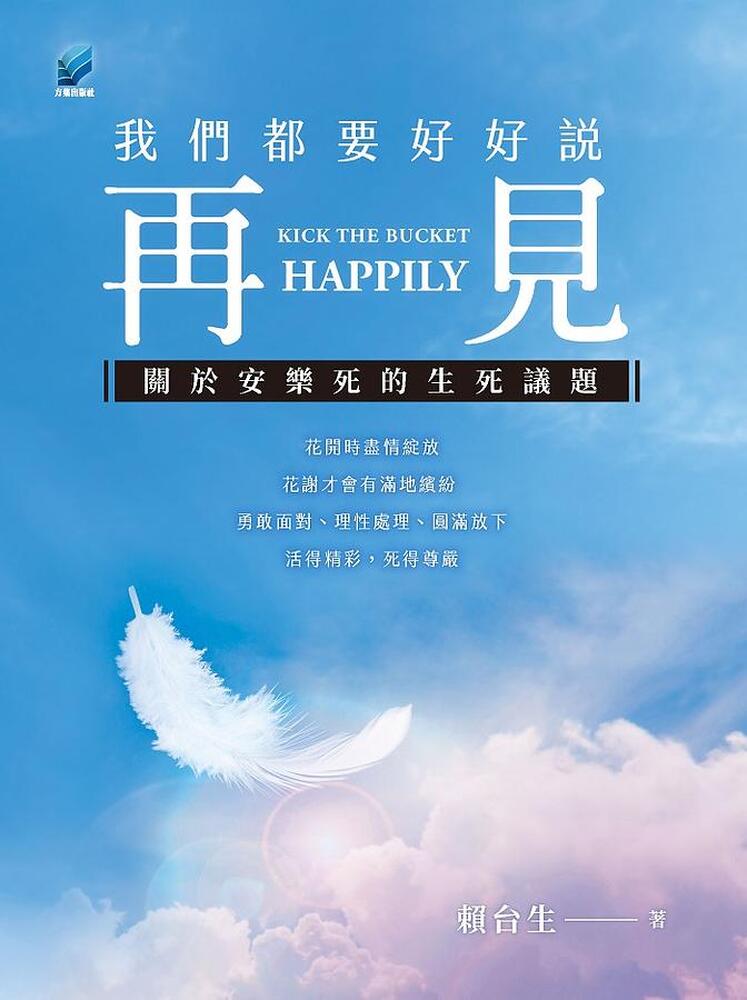《專題》醫療體系與安樂死:活著的尊嚴,還是無盡代價?
日期:2025-08-29 11:26:53

專題記者/劉錦龍/高雄報導
醫療照護的矛盾:延命與生活品質
在科技日益進步的今日,醫療不再只是延續生命的手段,更成為一場關於「活得如何」的深刻辯論。雖然現代醫療能延長生命,但延命不等於生活品質。昂貴的治療與無止盡的耗材,往往讓家庭背負沉重的經濟與心理壓力。對病人而言,活著不應只是「被迫生存」,而是擁有選擇、有尊嚴地走完生命旅程。尊重病人的感受,不只是醫療的責任,更是人性價值的體現。
病人自主權:法律保障與現實挑戰
台灣於2016年施行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,賦予病人預立醫療決定的權利,包括拒絕急救或維持生命的治療。透過「預立醫療諮商」,病人可與家屬共同討論,確保自身意願被尊重。
然而,制度的落實仍面臨挑戰。許多病人與家屬對法規細節認識不足,醫療體系也可能因慣性或利益考量而傾向提供過度治療。這提醒我們,法律雖保障自主權,但真正的尊嚴,仍需在制度運作中被細緻地實踐。
傅達仁的選擇:一場尊嚴的告別
2018年,資深媒體人傅達仁因罹患胰臟癌末期,選擇遠赴瑞士,加入當地「尊嚴」(DIGNITAS)組織,以安樂死方式結束生命。他曾公開表示:「能活多少天,權利在上帝手中;用什麼方式死,權利在當事人手裡。」這句話不僅道出他對生命的豁達,也成為台灣社會對「尊嚴善終」的深刻反思 A。
傅達仁的選擇並非逃避,而是一種勇敢。他在家人陪伴下,吟唱《奇異恩典》,走完生命最後一程。他的行動不僅喚起社會對安樂死的關注,也讓「善終」不再只是醫療術語,而是人性尊嚴的實踐 B。
安樂死與善終:國際經驗的啟示
安樂死在少數國家合法,並設有嚴格規範:
荷蘭:成人在無法緩解痛苦下可申請,需兩名醫師確認意願與病情。
比利時:成人與部分未成年人可申請,前提是痛苦無法緩解且意願明確。
加拿大:不可治癒重病患者可請求協助死亡,需知情同意並經多重評估。
瑞士:外國人可透過合法組織如 DIGNITAS 申請輔助性自殺,強調「活得有尊嚴,死得也有尊嚴」 。
這些制度顯示,安樂死並非鼓勵死亡,而是承認病人在生命最後階段的自主權。透過嚴謹的法律與醫療監督,社會得以在尊重個人選擇的同時,防止濫用與道德風險。
倫理的平衡:生命價值與自主決定
安樂死的爭議不在於死亡本身,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「活著」的意義。有人擔心制度可能被濫用,或以經濟考量取代倫理判斷;也有人認為尊嚴與自主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。理性分析應聚焦於:如何在保障病人尊嚴的同時,維護生命的價值與社會的倫理底線。
病人不只是身體的存在,更是有情感、有思想、有選擇能力的完整個體。他們的聲音不該被制度淹沒,而應被理解與尊重。
台灣的未來:理性與尊重並行
台灣已建立預立醫療決定制度,未來若進一步討論安樂死,應理性面對三大核心問題:
1. 如何確保病人自主,防止制度被濫用?
2. 如何讓病人與家屬充分理解醫療資訊,做出從容且知情的決定?
3. 如何讓醫療焦點回歸病人福祉與尊嚴,而非無止境的利潤追求?
借鑒荷蘭、比利時、加拿大與瑞士的經驗,台灣有機會建立一套兼顧法律規範、醫療監督與病人尊嚴的制度,讓病人在生命最後階段既安全又被尊重。
尊嚴是生命最基本的承諾
醫療不應只是流程與利潤的堆疊,生命也不該在病痛中失去尊嚴。討論安樂死,不是鼓勵死亡,而是深刻追問:在痛苦與無助中,我們如何保有人性?如何讓每個人都能自主選擇最後的時刻?
傅達仁的故事提醒我們,真正的善終,是在理解與愛中完成的告別。當社會以理性、同理與尊重面對這個議題,醫療才能真正服務生命,病人才不會淪為制度的犧牲品。
每個生命都值得尊重,每一天都應活得有尊嚴,每一次離去都應被理解與愛護。
這是我們對人性、對生命最深的承諾。